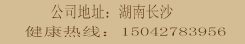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繁衍 > 事业和家庭终究是单选题吗戏剧时刻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繁衍 > 事业和家庭终究是单选题吗戏剧时刻

![]()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繁衍 > 事业和家庭终究是单选题吗戏剧时刻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繁衍 > 事业和家庭终究是单选题吗戏剧时刻
今天为大家推荐「戏剧时刻」短篇小说写作比赛「渴望之物」组入围作品,作者鹿仙贝的小说《那时我们有梦》——
这是一个科幻背景的情感故事,女儿和母亲、妻子和丈夫、妈妈和孩子,和许多现代女性一样,主人公夏罗在生活中有多重身份,不同的是,她有一个和虚拟影像有关的执着的梦。追梦路上,现实生活渐渐分崩离析……
虚拟电影公司造梦科技成立三十年之际,创始人夏罗把她的故事娓娓道来。
我们的人生不仅仅是眼前看到一幕。如果我们可以尝试着放下最表面的一幕,就会发现还有多重的荧幕在等待我们。那可是我们一直熟悉但无法指认的深层生活。严格来说,从个人潜能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它们也必须被看见。
那时我们有梦
鹿仙贝
温山曾跟我说,人生不像梦,可以一遍遍重做。
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我想……从头讲这个故事,那是在温南南出生之前——
那时我还很年轻。母亲常说我是在蜜罐里泡大的,脾气坏又骄纵,将来没人能受得了我。「受不了就别受。」我这样给她怼回去。其实那时我对三十岁后的人生还一点概念都没有,仿佛那是不存在的,所以就一点儿也不在乎。什么结婚啦,生孩子啦,根本没想过。
直到我遇见温山。
那时我在美国读研究生,刚和别人分了手,一个人跑去纽约过新年。跨年的时候总得做点儿什么呀,不能老窝在青年旅馆里,于是我就坐地铁去时代广场参加跨年。但没想到还不到四点,时代广场附近就都已经封站了。我又不甘心回去,于是就在那周围晃。路过一家恐怖电影主题餐厅好几次后,一个扮成德库拉男爵的服务员突然叫住我:「中国人吗?进来坐坐。」
那就是温山。
我走了进去,点了一个汉堡套餐。过了一会儿,德库拉男爵下了班,卸了妆,坐过来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大连人,也是留学生,在这儿打工。
我也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的梦想是做出一种……完全个人化的虚拟电影。温山说他没有什么梦想,就是自给自足,照顾好家人,如果可能的话,开一家自己的西餐馆。聊天时我发现他的发胶有点儿没卸干净,沾在鬓角,亮晶晶的。后来快到零点,餐馆打烊,大家准备离开,他问我是不是顺路,要不要一起走。
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想哭。到现在我还记得。不过我当然忍住了,和他告别,并计划等他消失后再随便到什么地方去晃会儿。但他看出了我的异样,说再陪我待会儿。结果我就没崩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一看到我这样就慌了,只得把我带到边上的一家24小时甜甜圈店坐着。我坐下后就继续哭,好像整个人都被一种巨大的悲伤给淹没了,也说不清为什么哭。
现在想起来那真是非常失态——在一个刚认识的人的面前突然爆发。
他问不出所以然,忽然也开始哭。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哭,我也想哭。」我一听就笑了,然后接着哭。我们两个人一起对着哭,就那样,不知不觉,新年过了。
后来那成了我和他在造梦师的第一段虚拟影片。
但虚拟影片和我的回忆有些差别。
影片里,我们还是想法子溜进了戒备森严的时代广场,参加了跨年倒数。新年水晶球落下的时候,我看到他亲了我的额头。他说:「希望以后每个跨年夜都能陪你度过。」我伏在他宽厚的肩膀上,眼睛看着纷纷洒落的五彩纸屑,什么也没说。
毕业后,我们都回了国,开始上班。我进了谷歌做脑机接口。他去了宝洁做快消供应链。我们都不太喜欢上班。折腾了一气,温南南出生了。我就没再回去上班。那几年我多了很多空闲的时间,看了很多的电影。我想我可能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虚拟电影这件事。
温南南两岁的时候,我找到以前的一些同事,开始创业。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电影是可以让我母亲平静下来的好东西。我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待着的时候,有一只耳朵是要支棱着听外面的动静的。外面过于安静时,尤其当临近中午,我就要出去检查下厨房,看看灶台上有没有嘶嘶冒烟的锅,母亲是不是又忘了关火就躲进卧室看电影去了。
她反正一直是不快乐的。只有在看电影时她才会忘记我的存在,不叨念我,不责骂我,不推搡我。
有时我想如果那次我没帮她打掩护会怎样。
一个下雨的冬夜有个男人来了我家。我看到他拿出一条金项链和一条银项链。母亲的脸红得像炉子里的火。他们在沙发上窃窃私语,热气腾腾。
后来男人走了,父亲回来,我什么也没说。
我还一直为我的机智骄傲呢。直到我在造梦师里再次看到这段回忆。
那大概是创业的第三年。我们做出了造梦师的第一个原型机。那时它就像个影音版的今日头条,你想看什么电影,它就给你推送一个什么。不过,和视频网站的「你可能还想看」功能不同,它会根据用户的个人喜好从很多的影像资源里挑选人物、画面、叙事等基本元素,然后把这些元素混成一部新的影片。早期的重混非常粗糙,基本上就是把两部电影剪在一起。实验阶段,造梦师最开始给我看的是《泰坦尼克号》和《革命之路》的混剪——杰克在船沉之际爬上了木板,和露丝过上了《革命之路》里的那种乡村中产阶级生活。杰克成了个无聊上班族,露丝成了不入流的糟糕演员。然后有一天,露丝又遇到了一个和当年泰坦尼克号里一样的「杰克」。两人难舍难分,决定私奔。可就在这时,露丝发现自己怀上了丈夫的第三个孩子。
这个粗剪片折磨了我半年。我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想知道为什么造梦师会认为我「想要看」这样的一个片子。那个过程中我有很多的设想——也许我是露丝,我的婚姻出了问题,片子在反映我内心的不安;也许我就是个观众,我想教育自己不要得陇望蜀。当然在反复观看的过程中虚拟影片的内容也在不断演变,原来两部电影的痕迹越来越浅。
直到有一天,它完全模拟出了我小时候那个陌生男人来造访的情境。
「妈妈,那是谁?」
「一个叔叔。」
「爸爸出去了?」
「你去练会儿琴吧。」
「刚才那是谁?」
「不是谁。」
就在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了母亲在婚姻里的苦闷。我看着画面里母亲渴望又悲伤的眼神,想起她在卧室里偷偷掉的那些眼泪。我自以为我很机智呢,小心地督促自己保持沉默。其实我多么恐惧,母亲要是走了,我去哪。母亲要是像《革命之路》的女主角一样执意要去巴黎,我怎么办;母亲要是像她一样执意要偷偷堕掉第三胎,我还会不会出生。
摘掉VR眼镜,我嚎啕大哭,一半为这个故事,一半为激动——造梦师终于成功了。它有了完全的智能,可以解读我的意识,还可以据此创造全新的影片。
我把这部虚拟影片放进了我的收藏夹。但后来不管我什么时候去看它,它的剧情都不再发生变化。我想,它沉淀了。
原型机出来之后我变得越来越忙。温山不喜欢我这样,虽然在宝洁他不断晋升,也变得越来越忙。我们请了爷爷奶奶来照顾已经上幼儿园的南南。
我曾经回答温山说,现在这个阶段在其它一切事情之前首先我想做的就是造梦师,此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也都不会做。他,我想他是妒忌的。他越来越沉默,好像从来就对虚拟电影这件事提不起兴趣。第一个智能虚拟影片做出来之后,他就那样,耸耸肩,表示他知道了,然后转移了话题。
他那个样子我是忘不了的。
然后有一天,造梦师拿到了A轮融资,条件是去美国建厂,把原型机从实验室装置升级成可以家用的小型机,以便商业化推广。
要说我没有一点犹豫就搬去了美国工作,那是不可能的。但那个时候家对我来说,已经开始变硬,南南和他的父亲、祖父母好像很坚硬地团在了一起,硬得像块石头,我被隔离在外。
但要把南南带去美国也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很清楚。就算我把他带去美国,也就周末能陪陪他。可能周末也见不上面。
所以,你看,所谓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根本是个伪命题。
我就从那时起到了美国。
现在回过头去看,好像可以说出一些道理来了(我好像在很多场合也确实这么说过),什么女性不能总用妻子和母亲这样的标签来定义自己啦;我们要把自己像茶叶包一样完全浸入水中才能发现自己到底是什么啦……都是假的。真正选择的时候我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些道理。可能人被使命召唤的时候就身不由己。
南南在大连也可以受到更好的照料。
但我内心深处是没有放过自己的。
离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想要重温和南南的那种亲密,造梦师都只给我同一个画面,画面是他一岁,然后我就要去创业公司上班,他很舍不得我,放声大哭。一个小婴儿,被圈在木质的围栏兜兜里,张着只有一颗牙的小嘴嚎叫。他靠着围栏,双手使劲儿地伸向我,眼里满是绝望。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真的相当艰难。我不知道造梦师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种东西,难道我对我儿子的愧疚还不够,需要用这种方式去一遍遍折磨自己,才能赎罪?才能心安?
我们并没有给造梦师设置竞争对手们爱用的用户成瘾机制。从第一天起,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创造多巴胺,让人兴奋,让人欲罢不能。我们要的是真实。你从内心深处真的想看到的东西,也许是很黑暗的。
也许是受了我的影响,我去美国后,温山也离开了待了十多年的宝洁,去开西餐馆了。
那段时间隔着大西洋和时差,我们的关系奇迹般地改善了些。但他仍然对我在做的事情抱有一种揶揄的态度。他说:「生活是个苹果,你不能只顾着找苹果里的虫,而忽略掉了苹果。」
在视频时他给我看餐馆的后厨。他教我如何用外表和触感判断瓜果是否健康,用纹理和色泽判断肉类是否新鲜。我很是为他高兴。
和南南的那个片段折磨了我一段时间。然后终于有一天,好像是造梦师的播放设备从VR眼镜升级到裸眼全息投影的那天。那天我带着疲惫回到公寓,坐在黑暗里,打开升完级的模型机。那时设备已经和现在的很像了,就是一只小小的耳挂,戴在耳朵上,它可以自动激活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不需要眼镜,也不需要耳机,就可以通过视网膜投影看电影。
我眼前再次出现了南南那张哭泣的小脸。
他的小手在使劲摇晃地够向我,我却什么都不能做。我再也不能把那团柔软的小东西抱在怀里了。我的手在眼前挥舞,却只能穿过空气。于是我开始跟他一起哭泣,哭了很久,直到画面里的他停了下来,好奇地看着我,仿佛穿过画面也能看见我。然后我看见围栏兜兜里的他迅速地长高、长大,一直长到他大概三四岁的样子。他穿着淡蓝色的小睡衣,手抻着木头床沿,揉着眼睛跟我说了第一句话:
「妈妈,为什么你半夜在洗脸刷牙?」
我想起来,这个回忆是有一次我回家过完春节要飞回美国公司的时候。
然后温山走进画面。
「爸爸,为什么妈妈在洗脸刷牙?」
「因为妈妈要去上班了呀。」
「昨天妈妈已经答应我不去上班了啊,怎么又要去,嘤嘤嘤。」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呀。」
镜头一转,还留着长发的年轻的我在卫生间擦脸。
走道上开始落下一行行金色的沙。
画面随后结束。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过来,我早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那也是造梦师最后一次给我和记忆基本一致的虚拟影片。
在影片里,我也没有留下来。
后来我又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我终于反应过来,可能我就是和大多数的母亲不同。
但那就是真实的我。
准备移居美国前,我、温山、还有刚上初一的温南南去了趟老虎滩海洋公园。
那是个秋天。晚上,我们在海边点燃篝火取暖。我拿出造梦师刚做出的第一款家用原型机,一个小小金色的耳挂,让南南戴上,然后等他告诉我看到了什么。我看见咸咸的海风让他的嘴唇干裂。
可他突然就把设备取下来扔到了地上,嚎啕大哭:「妈妈不要我了!」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却说不出来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温山指责了我两句,自己戴上了设备。结果没过五分钟,他也铁青着脸取了下来,还跟我说:「以后再也不要把这东西拿回家。」
他没有告诉我在里面看到了什么,直到今天也没有。
当时我有向他们解释,造梦师里看到的东西,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有点像梦,类似一张心灵地图。不管看到了什么,其实都可以让人更了解自己。但他们不听我的。
后来有一会儿他们都睡着了,我又偷偷爬起来,自己戴上设备。
透过火苗我看到许多影子:我、一个男孩、还有一个男人。当我和男孩牵起手,我是母亲;当我和男人牵起手,我是妻子。可当我离开火堆独自上路,我才看到我自己,那是一条孤单的长长的影子。
无论我走到那里,我的影子是不会离开我的。
然后画面一转,我又看见了母亲。
我看见自己正拿着笔记本电脑和卧病在床的母亲一起看电影。我们不发一言,静静凝视着同一个方向,那么专注,好像除此之外世界上什么别的东西都不存在。我知道那一刻母亲和我是在一起的。
我十八岁那年,母亲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去世。和霍金得的是一种病,渐冻症——病人的神经系统和肌肉系统会慢慢被摧毁,但心智仍然正常。近三年时间,母亲长期卧床,只能通过眼神和我交流。所以那段时间一有空我就拿着笔记本电脑陪她看电影,但总是很难找到她喜欢的片。她很难连续看上十分钟。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萌生了做造梦师的想法。我希望——当我不在母亲身边时,能有一种智能,可以替代我抚慰她的心,甚至比我更了解她,比她自己更了解她。完全符合她内心需要的陪伴。让她快乐,沉淀她的痛苦。
这个梦想始终陪伴着我,没有离开我。
从老虎滩公园回去之后我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我知道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造梦师的世界也将始终为我敞开。
篝火边的那个片段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虚拟电影之一,我把它放进收藏夹里,时不时拿出来翻看。每当我感觉到绝望,就有它提醒我,在脆弱的现实框架上,我仍然可以用想象力编织新的图案。
那天我甚至还产生了一个新灵感。在和工程师讨论后,我们试着开发了一款外置的投影设备,这款设备可以把一个人的造梦师虚拟电影投影到外放屏幕,方便多人观看。不过那个项目后来没有成,因为我们在测试阶段就发现——没有任何人愿意分享他的个人电影。没有任何人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现自己的内心。那会非常失控。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的工程师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观看「他的电影」,他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镜头会否出现他对某位女同事的性幻想。在真实的生活中,亲密总是有限的,隔着隐瞒、交换、妥协。
只有造梦师才能让我们与生活无限亲近。
造梦师的家用版一经推出立刻大获成功。
后来的故事你们也都知道了。公司经数轮融资后上市,直到现在。最近的这二十年来我们不断精修它的智能程度,让它可以无限贴近我们的内心深处,然后通过虚拟影视化表达,来释放我们在现实之下无法释放的压力。
这一点我曾坚信不疑——我们的人生不仅仅是眼前看到一幕。如果我们可以尝试着放下最表面的一幕,就会发现还有多重的荧幕在等待我们。那可是我们一直熟悉但无法指认的深层生活。严格来说,从个人潜能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它们也必须被看见。
后来就发生了南南的事。
我对他加入反人机内容交互协会一事并没有什么意见。那时他年轻,还在上大学,理想主义,充满抱负,我觉得是件好事。而且,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和大多数竞争对手不同,我们产品的出发点并不是用户成瘾机制。所以,即使他公开反对我,反对造梦师,我也从来没计较过。
我认为这是他选择和我连接的一种方式。
他对唯一一次使用造梦师体验的控诉我也看到过。就是那次在老虎滩的海边嘛,他将之称为老虎滩边的噩梦——我,背对着他在书桌前敲击键盘,打印机咔咔作响,不断吐出长长的纸条。突然纸条变成了黑色的石头滚到他面前,开始压迫他,直到他整个人都被封在了石头砌成的墙里。
他说他一直叫喊,一直哭泣,我却始终没有回头,对我自己的「暴力行为」浑然不觉,仿佛他完全不存在——「挣扎间我尖叫着扔掉了眼镜,却看到母亲责备的目光,仿佛我是某种出了故障的产品。」采访里我对他这句话印象很深刻。他确实是一个比较胆小的孩子。
从那之后温山确实就禁止他使用造梦师,直到他成年。
所以当下属跟我说南南报名了造梦科技美国总部的全球管培生计划时我还是有点吃惊的。我想也许这和我每年都给他们寄回一台新版的造梦师装置有关。不管怎样,反人机内容也好,好多年不理我不跟我说话也好,他始终是我儿子。
造梦科技也欢迎不同的声音。
我让他进了管培生项目。
由此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我谨慎地选择了在管培生计划的启动会上与他见面。他还有另外九十九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肤色各异的年轻人。我以为这种场合是安全的,对科技追求的狂热,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足以掩盖十多年来我们之间隐秘又巨大的鸿沟。我用对所有人一模一样的微笑与礼貌同他握手。他也朝我礼貌微笑。
我以为一切都很正常。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小心地观察彼此,借助造梦师的一点帮助,慢慢地靠近彼此。
谁知道几天后他就从旧金山大桥上跳了下去。
他最后的控诉你们也都知道了:「二十八岁的我,第一次发现,我的心我的渴望,都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容易破碎。造梦师的对我的诱惑空前巨大,忍受真实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艰难。我拒绝用我宝贵的真实生命力咏唱那个不属于人类的强大事物。但我好像已经别无选择……」
遗书的最后他说他理解了我。
那之后我还撑了一段时间。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深水炸弹。我见过一次。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去远海里看废弃潜艇的爆破。我当时还跑到甲板上等着,以为会有惊天巨浪。结果根本就没有。海面只是轻轻地动了一下,声音都没有,然后他们叫我进去看监控,潜艇已经粉碎。
他的死对我大概就是这样的影响。
我以为自己终于已经平静下来的深层生活又被炸得粉碎。
那之后我不敢再用造梦师。
到现在五年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的记忆不是图书馆里旧书,尘埃落定,它是一个鲜活的有机体,时刻受着现实经验的影响,时刻准备改变,只要我们能真正看到它。
我知道造梦师可以帮助我改变盘踞在人生里的那些阴影,重塑更美好的生活。
可我就是没有再拿起过它。
很想南南的时候我就去翻他以前发在社交网络上的视频。那里有很多真的他。谢天谢地。我可以将他们重放无数次,他的每一个笑容、每个皱眉、每一种无知,不管我怎么重放,都不会发生变化。
那件事之后不久我逐渐淡出了公司的管理层。到现在五年。
我想整个故事就大致如此吧。今年是造梦科技创立三十周年。他们邀请我,让我讲讲这三十年的故事。我想来想去,创业的这三十年固然很多的艰辛与奇险,但那不是我真正想说的……
总之,不知不觉,我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好了,现在我要去收拾一下见温山了。南南去世后我回了中国,在大连找了个地方生活。没有和温山复合,但我们是朋友。
一会儿在车上我要好好回忆一下在纽约时代广场的那个新年。真好笑,一有人搭讪,我就那么乖乖地走了进去。
我现在还记得他鬓角上没卸干净的发胶,他们和他的眼睛一样总在闪闪发亮。那感觉就像是在看一部颗粒电影——他的黑眼睛、黑毛衣还有窗外纽约的夜。黑色……像有毛衣包裹住我。那个瞬间,他就像上天送给我的一个新年礼物。那种瞬间拉进的亲密让我惶恐。
也许我就是因为这个而哭的。
对了,我还要好好想想,在我们的第一段虚拟电影里,当新年水晶球落下,当他吻我,当他说希望以后每个跨年夜晚都能陪我度过时,我为什么沉默。
作者:鹿仙贝(白癜风手术成果展白癜风品牌影响力单位
转载请注明:http://www.hujingahj.com/aqjj/36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