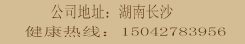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繁衍 > 愿有岁月可回首,不负时光不负卿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繁衍 > 愿有岁月可回首,不负时光不负卿

![]()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繁衍 > 愿有岁月可回首,不负时光不负卿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繁衍 > 愿有岁月可回首,不负时光不负卿
3.15
名人激励“意志坚”
今天班会课按学校要求召开“成功来自勤奋,付出才有回报”主题班会,通过学习张海迪事迹让孩子们做一个自立自强、不向命运屈服的人。
孩子们学习时都十分震撼!张海迪小时候因患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特的人生。15岁时,张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莘县,给孩子当起了老师。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年,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问世。《绝顶》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向“十六大”献礼重点图书并连获“全国第三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从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万字。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其一是“八十年代新雷锋”,其二是"“当代保尔”。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张海迪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供职在山东作家协会,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
看着被感动的孩子们,我想何不趁热打铁再拓展一下?这不正是培养我校“砥柱少年”精神之中的“意志坚”吗?于是,我给孩子们又挖掘了一些身残志坚的人物事迹。如:
海伦·凯勒(HelenKeller年6月27日-年6月1日)
19世纪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她在出生的第十九个月时因患急性胃充血、脑充血而被夺去视力和听力。年与莎莉文老师相遇。年6月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她以自强不息的顽强毅力,在安妮.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掌握了英、法、德等五国语言。完成了她的一系列著作,并致力于为残疾人造福,建立慈善机构,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美国十大英雄偶像,荣获“总统自由勋章”等奖项。主要著作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生活》、《我的老师》等。
年6月1日逝世,享年88岁,却有87年生活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
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WilliamHawking,年1月8日—年3月14日)
出生于英国牛津,年,霍金21岁时患上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卢伽雷氏症),全身瘫痪,不能言语,手部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动。但靠着自己顽强的毅力成为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
年3月14日,霍金逝世,享年76岁。霍金逝世后,引发全球各界悼念。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vanBeethoven,年12月16日或17日—年3月26日)
贝多芬被后世尊称为“乐圣”、“交响乐之王”。
贝多芬是世界的音乐家,也是命运最糟的一个。童年,贝多芬是在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家庭贫困,父母失和,造成贝多芬性格上严肃、孤僻、倔强和独立,在他心中蕴藏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他从12岁开始作曲,14岁参加乐团演出并领取工资补贴家用。到了17岁,母亲病逝,家中只剩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已经堕落的父亲。不久,贝多芬得了伤寒和天花,几乎丧命。贝多芬简直成了苦难的象征,他的不幸是一个孩子难以承受的。即使如此,贝多芬还是挺过来了。他对音乐酷爱到离不开的水准。在他的作品中,有着他生活的影子,既充满高尚的思想,又流露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对美丽的大自然他有抒发不尽的情怀。说贝多芬命运不好,不光指他童年悲惨,实际上他的不幸,莫过于28岁那年的耳聋。先是耳朵日夜作响,继而听觉日益衰弱。他去野外散步,再也听不见农夫的笛声了。
从此,他孤独地过着聋人的生活,全部精力都用于和聋疾苦战。贝多芬活在世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能给他安慰的只有音乐。他作曲时,常把一根细木棍咬在嘴里,借以感受钢琴的振动,他用自己无法听到的声音,倾诉着自己对大自然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他的《命运交响曲》就是在完全失去听觉的状态中创作的,是贝多芬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它的主题是反映人类和命运搏斗,最终战胜命运。这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年3月26日,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音乐巨人与世长辞,那时他才57岁。贝多芬一生是悲惨的,世界不曾给他欢乐,他却为人类创造了欢乐。贝多芬身体是虚弱的,但他是真正的强者。
孩子们还想起了我曾经讲过的69岁“无腿老人”夏伯渝成功登顶珠峰的事迹以及“钢铁战士”保尔·柯察金不怕困难不怕病魔的事迹。
相信今天的班会课通过名人激励这一途径能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意志坚”的种子,未来的日子他们不管道路平坦曲折都能走得更远。
3.16
这些孩子算不算患了“自然缺失症”
上周末布置孩子们看梅花,并写一篇有关梅花的生活日记。交上来的日记不尽如人意,如要求的从远到近的习作顺序,梅花的外形、颜色、香味、精神这些正面描写,蜜蜂、游人等侧面描写以及的真情实感等,很多孩子都没有做到。最不靠谱的是从网上胡乱摘抄了说明文或者散文。于是我让不合格的重写再写。
上课时我统计了“看梅花”这一实践活动作业的完成情况很是吃惊。班里48人,两人没有参加,参加的46人中感受到梅花漂亮自己也很开心的仅有10人,其他孩子没有什么感觉,觉得看不看都无所谓。面对那么惊艳带着暗香的梅花他们竟然没感觉,好冷血呀!我又抛出一个问题“如果看梅花那段时间让你自己规划,你会用来干什么?”结果20个孩子选择宅在家里看电视,看韩国综艺节目,看动画片,看喜剧电影等等,其他的选择宅家玩手游、看抖音、吃零食、睡觉或者瞎玩儿,还有的没有想法,无所谓的样子。
我和办公室马老师聊起这件事,她上六年级的儿子也是不愿意出门看看花看看春天,也是希望宅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和朋友玩儿。
一个不热爱大自然的孩子会有什么后果呢?我做了百度,这样一篇文章让我深思:
——失去自然的孩子:我们更喜欢在屋里玩,因为屋里有电源
导读:
“孩子对于自然的喜爱是天性,全都烙刻在基因里,但前提是你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接触到自然。”——刘芝龙
来源:“光明社教育家”
作者:王梦茜
重拾自然教育,不做林间最后的小孩
当下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自然教育?
“孩子就像需要睡眠和食物一样,需要和自然的接触。”美国记者兼儿童权益倡导者理查德·洛夫提出“自然缺失症”这一概念,揭示了儿童与自然间关系的断裂。
洛夫指出,儿童与自然的疏离会导致身心健康的多重损害,造成感官逐渐退化、体重超标、注意力紊乱和抑郁等病态,间接地损害儿童的道德、审美和智力成长。
是谁在儿童和自然之间筑起了藩篱?
城市化、教育分数化、娱乐电子化,这些因素无疑给儿童接触自然制造了多重障碍,但“自然缺失症”的病因更主要在于自然教育的缺位。
要“对症下药”,便需回归自然教育本身。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相关文件的出台,学生和老师有更多的机会将书本知识与真实自然、现实生活建立联结。
不少学校在校园内外构建起自然教育的绿色空间,挖掘自然教育在学科渗透中的可能性,但学校自然教育目前仍存在着尚未被普遍纳入教学课程体系、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相关专业知识储备有限等瓶颈限制。
校外,越来越多的民间自然教育机构、公益组织、科研单位、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等加入自然教育的行列,寻求治愈“自然缺失症”的中国“药方”。
他们的探索与实践让我们看到——自然空间不一定只在乡村里,也能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自然教育不一定只在山野中,也能存在于每个家庭的生活方式与每个学校的绿色空间之中。
当下,儿童是否还可以拥有亲近自然的空间、实践和体验的常规渠道?
自然教育打开了一扇窗,我们看到了一束光。但能否向着光继续往前走,需要所有人的努力,学校要努力,家长要努力,孩子自己也要努力,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原文:
当教育远离自然,孩子缺失了什么
文
王梦茜
“她当时刚学完一篇有关燕子的课文,跑来问我哪里能找到燕子,她说她太想看一看燕子是什么样的。”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创始人王愉回忆起女儿“找燕子”的故事时说,“后来我开车带她去郊外,在车上她终于看到了燕子飞过的身影。”儿时常见的动物,十多年后却需要特地到郊外才能看到,王愉感受到,当下儿童亲近自然的空间与渠道似乎越来越窄。
“他们更喜欢在屋里玩,因为屋里有电源插座”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萤火虫,分不清树的种类,认不得虫,没碰过草地,也没有看过银河系。那他们的童年在忙什么呢?忙做功课、忙挤校车、忙补习,仅有的一点空闲,看看电视和漫画书也就不够用了。”作家三毛称这些孩子为“塑料儿童”。
我们身边也存在这样的孩子:除去在学校的时间,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宅在家里,和电子游戏或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为伴,他们对外界的自然不具备应有的好奇心,对身边的自然事物缺乏最基本的兴趣。
他们知道课外书上亚马逊雨林里的稀有物种,却不知道家里餐桌上的蔬菜名称,他们看过电视电影里的麦田、菜园,却没有亲身体验过下田、抚摸过一株禾苗......他们更喜欢在屋里玩,因为那是有电源插座的地方。这些现象,被美国记者兼儿童权益倡导者理查德·洛夫称为“自然缺失症”。
“生活在高度重复的城市环境中,人的感知能力越来越弱,由此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感觉综合失调。打个比方,有个杯子在你面前,你去拿它,却没拿住,是因为你对它的位置判断不正确,你的视觉和触觉无法协调起来。”植物私塾创始人张新宇表示在自然教育的实践中,他接触过许多感觉综合失调的孩子。
年10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首份《世界视力报告》显示,中国城市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达67%,他们推测这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化和学校教育系统等原因造成的。
乡村也并非“自然缺失症”的空心地带。年8月20日,中国儿童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中国儿童发展报告()——儿童校外生活状况》。报告显示,周末,乡镇农村儿童的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18分钟)明显高于城市儿童(88.40分钟)。
“除了近视,农村‘小胖墩’也越来越多。”“U然”自然教育联合创始人郭海岩告诉记者,据成都市疾控中心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成都农村地区儿童肥胖率不断上升,其中,在部分年龄段甚至超过了城市儿童肥胖率。年,在8岁儿童年龄段,城市女生肥胖率为8%,而农村女生肥胖率则为9.7%。
“自然缺失症”并不是一个医学术语,它概括了一种社会趋势,让人们得以从这个视角去思考自然对于儿童成长的影响。理查德·洛夫指出,儿童与自然的疏离会导致身心健康的多重损害,造成感官逐渐退化、肥胖率增加、注意力紊乱和抑郁等病态,间接地损害儿童的道德、审美和智力成长。同时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直接接触自然对于注意力缺失、多动症、儿童抑郁症、压力管理都有治疗的功能,对认知能力也有改善。
盖娅自然学校校长张赫赫在活动中曾遇到一些孩子,他们往往有控制情绪的困难,容易发怒。但随着到大自然中,与伙伴们一起进行一些活动,他们的情绪往往会逐渐平稳,与他人相处也会变得容易起来。
“在家庭或学校环境中,由于长期被单一尺度度量,一些孩子可能会处在焦虑、恐惧等不适情绪中,因此别人无心的一句话就会把他们的情绪点燃,甚至会以暴力的方式来对待别人。而大自然里的活动,往往不设定唯一的评判标准,大家更容易放下彼此,接纳包容。”
恐惧、对抗与不知所措
“孩子对于自然的喜爱是天性,全都烙刻在基因里,但前提是你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接触到自然。”台湾大学植物学博士、林奈实验室创始人刘芝龙说。
年,厦门学生张欣窈研究的课题《“自然缺失症”现象调查与对策研究》,获得第27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其中有一个问题——“有一项关于‘我们身边的生物’的调查,你到哪里完成这项作业?”对此,88%的同学回答“上网找”。他们对自然的了解大多数来源于网络、电视等信息媒介。
当孩子与自然的空间距离增大时,心理上的距离随之拉开,他们对于自然的态度、认知也可能产生偏差。久而久之,自然逐渐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
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和科技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云南植物考察学生科普夏令营”,每年都会送50余名澳门中学生来云南参观。曾为该夏令营活动做讲解的海螺发现,面对园内多样有趣的植物种类,这些中学生兴致很低,“参观期间他们一直在聊天、抱怨,要求休息和早点离开。注意力难以集中、对周围变化显得漠然是这些学生留给我们的整体印象”。
“当孩子们重新回到大自然系统中,大多数人还是有好奇心的,但是他们往往不知所措,并不知道该怎么跟自然打交道。”张赫赫以电影《阿凡达》打了个比方——当双腿瘫痪的前海军陆战队员,进入阿凡达的躯壳中,他走路跌跌撞撞,十分莽撞,“这些重新回到自然中的孩子,就跟那个角色一样,显得笨手笨脚,不知道如何与自然相处”。
“他们觉得泥土是脏的,看到任何昆虫都会害怕,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虫子会不会咬我’......”在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自然教育总监王西敏看来,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对大自然的恐惧十分明显。
一次夏令营活动,他带孩子们穿越一片树林,在一个池塘边看见一条铁线虫,孩子们并不认识这种虫子却纷纷表示要打死它。“那天晚上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为什么孩子想把它打死,可能是害怕不认识的动物伤害他们,也可能是觉得这个动物比我弱小,或者就是单纯的不喜欢,这种看待自然的心态是应该去改变的。”
“他们和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到后面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适应和亲近自然了。”王愉认为,从表象来看,孩子与自然的不亲近表现为,孩子在自然中会没有安全感、很难放松、不知道如何观察、不知道怎么去玩。她曾目睹一个孩子看见蜻蜓时的场景——哇哇大叫,十分惊恐,“我当时很惊讶,因为不管是飞行的姿态还是身体的结构,蜻蜓都属于自然中特别美的一种昆虫,很难让人产生恐惧感”。
当“自然缺失症”儿童长大之后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刘悦来,在景观设计专业的教学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景观设计是一门与自然关系非常密切的学科,但学生们对自然却并不敏感。
“认识自然是景观设计的基础。做设计时,我们首先要分辨哪些东西是能够设计的,哪些东西是不能设计的,如果连这些都不了解的话,你的作品反而会让更多的人成为受害者。现在有很多园林景观,把一些本来很自然、质朴的地方,变成很‘奢侈’的设计,最后产出一个个‘绿色荒漠’。”
“我接触过许多生态学方向的研究生,有些人采集动植物标本时一点都不手软,见到植物就采,见到蝴蝶就抓,采集的标本也许对他们的科研并没有多大作用。”王西敏口中的这些年轻人虽然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学习工作也与自然息息相关,但他们对自然缺乏情感、对生命缺少尊重。
理查德·洛夫指出,儿童需要对大地拥有强烈的依恋,这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健康,更是为了让他们成年后拥有保护自然的责任感。而童年缺乏自然经历的人,对环境往往会更加冷漠,很难培养出良好的环境态度和行为。
提到“自然缺失症”的后果,王西敏从环保主义者的角度对此表示担忧:“如果我们从小没有在孩子们心目中种下对于大自然的情感,那么以后希望他们
转载请注明:http://www.hujingahj.com/aqjj/7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