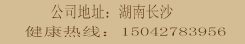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种类 > 参加高考的孩纸们,被霍金的祝福撩拨得热血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种类 > 参加高考的孩纸们,被霍金的祝福撩拨得热血

![]()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种类 > 参加高考的孩纸们,被霍金的祝福撩拨得热血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种类 > 参加高考的孩纸们,被霍金的祝福撩拨得热血
那时频道不多,时间受限,收看效果常常被羊角似的天线左右
第一次见电视机,是肚皮多少能吃饱了的年春节,新衫罩了破衣,父亲带我去人声沸鼎的青年会。二楼有个不大的房间,挤挤挨挨是人,正前方是一只小匣子,居然在播放黑白电影,惊讶得我寸步难移。再一次见这场景,是十五年以后,西湖牌9英寸木壳黑白电视机问世,杭州人热血沸腾。那是我年护送一个在煤井下工伤瘫痪的“插友”回杭后的第二年,也是探亲。那“插友”借住西湖饭店,房间满满是人,电视正映播《牧鹅少年马季》。我能清楚记得电影片名,记得那一晚的笑声,因为我觉得空气不再沉闷。但那几年买电视机全靠“后门”,人情投资,虽已技巧谙熟,一票依然难求。一旦哪家有了电视机,不仅是娱乐的寄托、亲友人气的提升,更是身份的象征。当然,“娱乐说”只是晚上短短三四个钟头,全天候的功能是瞩目的摆设。年9月,我工作调回杭州,12英寸的电视机盛行一时。虽然只能播放黑白电视,凭票依旧。好在有了进口货,供应略有宽松,但价格不菲,让不少工薪阶层倒吸凉气。有亲戚搞到一张“索尼”票,转让给我。我的老父为此喜气洋洋,尤其晚上,朋友闻信上门。但那时频道不多,时间受限,收看效果常常被羊角似的天线左右,时有与剧情无关的“下雪”,须用手转动天线。好在不用担心交费,看得心安理得。多花了5块钱,年的秋末,那台内蒙古产的平屏彩电,归我了有一天我发现天线被焊接过了,应该是老父在白天转动时折断的。我难以想象70多岁的老父,拿了煤炉上烧得半红的烙铁,在楼梯上下。我假装没有发现,一直到他去世。可惜父亲没能看上彩电,他走时,刚面世的彩电稀罕得如同“洛神”。父亲走后的第二年,彩电兴起。不久,“谣传”来了:紧缺的家电,要实现价格“双轨制”。你能买得起,有市场价。当然,计划价也有,能买到,是你的造化。这也意味,有计划指标的,必定能赚大钱。于是,彩电商店,连陈列都缺了样品。特供仍有,譬如延安路上的侨汇商店,虽然“风声鹤唳”,偶尔也有货源。那时我手上正有一些侨汇票,够买一台彩电。某日下午,闻风而去,前胸贴了后背排队,秋日中浑身是汗。眼看柜台内开票的将彩电一台台开了出去,呼儿嗨呀,眼睛都红了。还没轮到,彩电售罄,我只剩傻瞅。橱窗有台样机,尽管男营业员声嘶力竭说“不卖的!”众人仍不死心。有人一支接一支将香烟递过去,求高抬贵手。我灵感突生,将一张5块纸币卷成烟样,塞给他,我说我不抽烟,你就买包吧。就5块钱哦,年的秋末,橱窗那台内蒙古产的平屏彩电,就归我了。也就小小十年,当路边促销的“彩电”成队排列,女孩子笑脸相迎,说大哥,你买一台吧。我就会想起,那个臭汗夹背的黄昏。台湾客人每逢洽谈商事,也有奉迎我的,言过其实的大多被我婉拒年4月,离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不到一年,我表姐从台湾来杭。居民干部和我姑妈说,大妈你嫑怕了,现在台湾有亲戚,是蛮光荣的事情。表姐儿时曾在城隍山遇一占卦,那“铁口”说她日后是要出远门的。没想到,这一出三十五年,魂牵梦萦。表姐一口软软的杭州话,她说在加拿大经商时得到签证,辗转而来。途经韩国时,一度被阻。她恳求:我老娘80多岁了,我不能等她没了再去。次日,表姐来我家,先规规矩矩去了派出所,由户籍警陪同上门。她说,这是我从小生活的外婆家。正因为这次探亲,感觉良好的表姐决定将工厂落到深圳。于是,来杭州成了常事。于是,她儿子也来了,儿子的同学也来了。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其中的X和N先生,也算那时来内地的台商典型。X与N是台北一家公司的两位老总,第一次来杭时,表姐的儿子嘱我多多协助。那时,一听台湾来人,都当大佬。我也提醒这两个比我小不了多少的“老总”,切忌做“淘金”的“空手道人”。每逢洽谈商事,也有奉迎我的,言过其实的大多被我婉拒。有一位颇有神通,据说,破省军区的大墙置业,就他岳父点个头的事。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笕桥机场迎接再次来杭的X先生,车转三桥址直街,他先接来一个20多岁的漂亮女人。两人在后座,先海聊这女人的安排,后来就搂一起了。也许算我作梗,也许是这仁兄急于见钱的投入,最终没谈成。有一位是我远房亲戚,闻讯找来,说诸暨某厂新产品研发后,没钱扩大生产,要我设法周全投资。X和N倒也有意,一起去了那农民伯伯的厂里。那厂长初见西装革履的台商,有点羞涩,避了,由工厂的技术“大拿”,我的亲戚出面。X先生指了一位貌美发秀的女士问我:长得漂亮么?台湾女士不比杭州的差。当晚,厂长来宾馆和我聊天,正是隆冬,我说洗个澡吧。说出来有点寒酸,澡后的浴盆,飘了一层“盐豆浆”的皂花。这就是当今踌躇满志杀向国际的私企老总,他们的起家,着实有人不知的艰辛。可惜,很顺的投资,最终栽在我亲戚那个18岁的儿子手上了。他吹嘘能高出官家的兑换率帮X先生换几百美金,结果,美金拿去,鸟枪都打不着了。文化的一脉相承,与开放时大环境的优越,让X、N对杭州青睐有加,计划搞资本风险较小的养老业。几经洽谈,看中了钱江大桥(一桥)南堍某轴承厂疗养院。设施尚可,园林不错,短缺资金。两方签约,X方承诺五年内投入资金改造,分批引入台湾老人养老。此后的工作,倒也扎实。我见过台北的广告,半张报纸的文字图片,标题“你就是神仙”。第一批养老团来了,有夫妇同行,有国军退伍老兵,也有对内地好奇的生意人。朗风丽日的金秋,X先生满面春风率人下机,指了一位貌美发秀的女士问我:长得漂亮么?我就是要让你看看,台湾女士不比杭州的差。不过,为人踏实的N先生却因老父去世,没来。渐渐的,一心想挖口“大金矿”的X先生,离我远了。一年后,他从成都来信,烫着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金字的贺年卡上,赫然印了他副总经理的头衔。两年后X先生从上海来信,他又在浦东当了某某房地产公司的副总。某日,X坐轿车来看我,他搂了我肩,告诉陪同:这就是第一个帮我闯大陆的杭州老大。席间,我问起X太太,一个为他生养了一对孪生女儿和一个儿子的漂亮女人。X悄悄说:我在上海违反计划生育了。我笑而不语,当我第一次听他说大陆的女孩子好大方时,知道会有这一天的。电话又似企鹅伸长脖子的排队,轮到了,服务生说,美国无法通话,只能电报年春天,某日,我下班,莫名其妙的念头,想去看我姑妈。姑妈和儿子有点小过节,住在我表侄家。我见姑妈在昏睡,叫她,唇蠕动,人没醒。表侄说,她刚蛮好的,解过大便哎。我说坏了,赶紧叫医生!我姑妈心脏不好,老人解大便最易引发心力衰竭。侄医院,医生赶到,救不过来,老人家驾鹤西去。姑妈有一子一女,我表哥近在咫尺,表姐远在台湾。那时没有电话,我想先去表哥家告知,再电话通知表姐。也就一转念,我担心表哥赶去会冲突,决定先打表姐电话,再陪表哥前往。打长途要去惠兴路电信局营业厅,也许刚改革开放,通信一自由,人头攒动。那时,大陆与台湾没有电话直达,我通过香港九龙某公司张某电话转告。填表,排队、审表,挨号等待。看不多的几个电话间,人进去,不出来,有点像内急人在公厕望眼欲穿。近1小时,服务生叫我,说到某某间接电话。那是一位小姐的声音,操国语,她说张先生不在。我再填我表姐的女儿信息,她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又似企鹅伸长脖子的排队,轮到了,服务生说,美国无法通话,只能电报。退出队伍,重填电报表,人到这境地,脾气都会好的。我到电报柜台排队,轮到后,又告知要填写英语。那时的服务,完全不是如今,服务生毫无帮助余地。一声长叹。离开闷热嘈杂的营业厅,我在清冷夜色中骑车疾奔,去找“夜大”时英语最好的女同学钱某,她住凤起路。好在同学的丈夫并不介意我晚上找他的老婆,我假装吃饱了饭,等她一字一句翻译。再赶回电信局,排队登记。登记,挨号,初装费多元,顶我5个月工资九点多,电报发出,怕耽搁时间,我直奔表哥家。发誓不登儿子门的表哥听说娘没了,赶紧和我前往。他看到灵堂布置好了,惊讶问我:姆妈是什么时候走的?我说五点多。表哥急了:现在几点?我是儿子,就一个杭州,几步路,为啥不通知我?你嫌我穷!唉,有口难辩。有谁在那个夜晚,见过人头攒动的电信大厅?见过我饿了肚皮狼狈不堪的奔波?只有电话,一个在急难中令人抓狂的电话,一个当今一摁机键就能将语言传之万里的电话。但是,当你连命运都无法掌控之时,奈何电话?两年后,崔健的“一无所有”响彻街巷,电话安装的“杭儿风”,令多多少少“一无所有”但想改变命运的人热血沸腾。惠兴路电信营业厅又排起了长队,登记,挨号,初装费多元,顶我5个月工资。但一句“某某家装电话啦”,真就是身份的象征,诱惑极大。那是“一块瓦片落下,会打着三个经理脑袋”的年代,我也承蒙朋友推荐,任某公司“副总经理”,上级公司的大佬是某某要人的儿子。我心发虚。一是所在的工厂不许我调转;二是上级公司名头太大,冠以“中华国际”。说穿了,就指望买卖计划指标,赚大钱,我不是那料。每次治保主任在离我家两间门面处立定,丹田发力,大叫我有电话时,我总担心她会冒出“曹某某总经理电话”,震下几片瓦来。居民区公用电话就装在治保主任家的堂前,我接电话,主任闲着也是闲着,一旁跷脚细听。好在不久,我家也有了电话,不过,非我出钱,是同一楼梯的沙姓邻居,沙孟海的侄儿。沙的“磁场”绝对比我强,但低调实在,他太太在外做点生意。我们两家的板壁房间,隔了楼梯,门对着门。他俩经常在外,电话装在我家外房间。不久,我任职的公司要转驻他处。我借口工厂调转不成,不能为公司创利,离开了。热闹一度的电话,就此冷却。如今,我家电话也算是“冷却”的,那是被手机抢了风头的搁置,又是一番天地。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hujingahj.com/aqly/55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