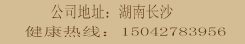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形状 > 霍金当一个人的希望降到零时,他才真正珍惜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形状 > 霍金当一个人的希望降到零时,他才真正珍惜

![]()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形状 > 霍金当一个人的希望降到零时,他才真正珍惜
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形状 > 霍金当一个人的希望降到零时,他才真正珍惜
▲年12月10日,霍金在耶路撒冷布卢姆菲尔德科学博物馆发表演讲的资料照片。新华社/法新
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据英国媒体报道,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去世,享年76岁。
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万神殿里供奉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霍金不在最耀眼的之列,却很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位。虽然他是一位轮椅上的囚徒,但他的人生却比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丰富、精彩得多。虽然有太多的光环和传说围绕着他,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分辨出某种简单而重要的东西,即集人类处境的两个极端——躯体的渺小脆弱与思想的广袤无垠——于一体的动人情形。
霍金的存在已不再具有物理学上的意义,而是具有另一种意义——成为人类与不幸命运抗争的象征。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1
斯蒂芬?霍金在76岁的年纪上去世了。虽然他是一位轮椅上的囚徒,但他的一生却比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丰富、精彩得多。这个时代的科学研究越来越依靠昂贵、复杂的仪器以及成百上千人的合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不再是科学家,而是以科学为职业的工匠,尽管有的还是能工巧匠,因为他们的研究已不再受热情和兴趣驱使,而是为生计所迫,受利益驱使。在霍金身上,还多少保留着那种业已消逝了的科学家的古老形象:高傲,专注,特立独行,激情四射,且智力超群,虽然似乎谈不上清贫寂寞。
随着《时间简史》被译成中文,霍金在中国开始渐为人知。这还是年代中期的事。年的来访则使他变得广为人知。其实,早在年晚春,他就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中国之行。当时我还在科大念大三。这位非常活跃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来到合肥前,肯定还到过中国的其他地方,但我只知道他来到了科大不怎么漂亮的校园里,因为海报已经张贴在图书馆前的布告栏上。同学们都有些不敢相信,像霍金这么既不便行走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怎么说来就来了呢,且来到了偏居一隅的“裤子大”(在合肥方言中,科技的发音与裤子很接近)!现在想来也不奇怪,当年科大的天体物理和宇宙学不但国内有名,在国际上也算是活跃的。
霍金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落成不久的水上讲演厅。所谓的水上,是指建筑物的主体建在一个当时有水、如今早已干枯的小池塘上。谢灵运的诗句“池塘生春草”是很能给人以诗意遐想的,但这个池塘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是光秃秃的,与任何诗情画意无关。水上讲演厅可以容纳二百号人,是除大礼堂外容纳听众最多的地方,非常适合做大型的学术报告。
2
霍金在助手的簇拥下进场了,果然如传说的那样坐在轮椅上。他系着领带,穿着整洁的白衬衫,瘦削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大框的金丝眼镜,看上去相当年轻。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还夹杂着少许的叹息声。那时霍金只有43岁,刚刚写完了《时间简史》的初稿,声誉正处于持续增长中,但还没有成为大众明星,因此几乎看不到记者在场,也看不到令人厌恶的、闪个不停的闪光灯。轮椅停在了讲台的右侧。主持人介绍说,霍金先生是最年轻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的卢卡斯讲座教授。这两个头衔对于在场的人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了。在整个报告中,霍金的脑袋朝一边歪斜着,目光似乎始终看着一个地方。
这种场合的报告带有普及性质,难度不是很大,现场还有一位天体物理小组的老师做翻译。那位老师五十左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已经是正教授了(在那个年代,正教授还是比较稀罕的)。他并不是翻译霍金本人的话,而是翻译霍金助手的话。当时霍金还没有完全丧失语言能力,为记者所津津乐道的金属合成器的声音则是从中国回去以后的事,但别人已经听不懂他的话了,只有他的助手听得懂。助手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短袖的深色竖条纹衬衫,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与他那副稚气的娃娃脸颇不相称。
大概是很少出国的缘故,没过多久,那位老师便出了一个错,接着又出了一个错。同学们便用掌声把他轰下了台,又用掌声将指出错误的人请上台做翻译。对于这一戏剧性的插曲,旁边的两位英国女学生感到既新鲜又好奇,而她们的老师依然一动不动,脑袋像先前一样斜靠在椅背上,脸上没有任何的反应,仿佛完全没有看到这一幕。也许是疾病在起作用的缘故,我还从未见过如此专注的表情。
二十多年后,我已经不记得报告的主要内容了。但有一个观点因为印象深刻,至今仍然无法忘怀。这个观点的大意是,在一个收缩的宇宙中(在年代,宇宙加速膨胀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由于科学界已经发现宇宙在膨胀,因此认为宇宙在引力作用下减速膨胀便是理所当然的),时间可能会发生倒转。举一个例子,在膨胀的宇宙中,杯子掉到地上,摔成了碎片,而在收缩的宇宙中,散落在地上的碎片则会“破镜重圆”,成为一只完好的杯子。这话如果出自其他人之口,我会认为是痴人说梦;但既然大名鼎鼎的霍金这么说了,我自然是十分信服(其实是连怀疑的资格也没有)。后来在一首《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诗中,我还描述过所谓“时间倒转”的情形:
而尼罗河小花蛇的一吻
复活了克莉奥佩特拉女王
先与安东尼将军打情
再与凯撒大帝骂俏
后来我在读《时间简史续编》时,意外地发现霍金在书中否认了这个观点。这当然令我沮丧——假如宇宙有朝一日真的发生收缩,而时间真的开始倒转,人们真的越活越年轻,在子宫中死去,那该是多么有意思的事!
我自觉这场报告听懂了一大半,于是又赶去听下一场只有几十人的小报告。小报告属于专业交流,没有翻译。我什么也没有听懂,只知道主题大概与黑洞形成有关。霍金依然斜靠在椅背上,表情依然那么专注。由于距离较近,他的声音倒是听得更清楚了。这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就像喉咙里卡了一枚鱼刺,又好像患了感冒的女人捏着鼻子说话,我瞧着霍金的大耳朵,心想。可惜,当时的我根本不具备理解他人处境的能力。我没有去想这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声音有些特别,仅此而已。由于霍金本人表现得若无其事,我便也觉得这没有什么。再说,我还想弄明白——当然是白费力气——他究竟在说什么呢。
3
很多年后,当我读一本有关渐冻人的书时,这一场景又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此时我才感到霍金的专注和若无其事多么不易。这位渐冻人来自瑞典,曾经是电视台的女主播,名叫林奎斯特(Ulla-CarinLindquist),她在临终前这样写道:
我想说的话似乎到了鼻腔那儿就下不去了。我感到自己的颚部好像裂开了一般。软颚似乎在不断地松懈……我的嘴现在也只能呼呼发出一些不可识别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留声机的唱片在用错误的速度播放一样。
我的两个比喻都不准确。就好像唱片在用错误的速度播放,这个比喻才是恰当的,霍金就是用这种声调说话的。但这个比喻是另一个人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尽管同样是ALS(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患者,疾病在霍金身上的进展却要缓慢许多。这是他的幸运,上苍似乎有意眷顾于他。然而这依然相当于一种慢性活埋。斯蒂芬?霍金可以精确描述恒星垂死阶段的喘息,可以无限逼近宇宙大爆炸绝对灼热的开端,却不愿过多地描述自己的悲惨遭遇。多亏了这位坚强乐观、感情细腻的瑞典女性,使我能够体验到这一疾病所带来的点滴折磨和强大而不可逆转的窒息感。
年2月14日晚,32岁的霍金向科学界的同行报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黑洞不黑,它也能向外界辐射能量。这种辐射后来被命名为“霍金辐射”。它是将量子力学引入由引力理论主宰的黑洞研究的产物,虽然迄今尚未被观测证实。当霍金在演讲厅里介绍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时,在演讲厅外的茶室里,他的妻子简听到了两位清洁女工的对话:“里面那个人,就是那个年轻的家伙,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是不是?”“是啊,他看上去好像快要垮了,连头都撑不住了。”这样的对话自然令人不快,但有时候庸人的见解里也包含着朴素的真理。事实上,人类文化中最灿烂的部分往往是由那些不幸的人或者没有多少日子可活的人创造的。两千年前,司马迁在其感人至深的《报任安书》中就表达过这一见解。只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的科学界,这样的例子不太常见罢了。弥尔顿失明时已经人到中年,贝多芬在得知耳疾没有治愈的希望时,已经是一位年轻的大师,而霍金在事业刚刚开始的21岁,即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只是由于特殊的运气,他才得以活这么久。在这以前,他是一个偶尔酗酒、有点厌倦生活的聪明人;在这以后,他变成了一位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的勇士,诚如他自己所言:“当一个人的希望降到零时,他才真正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在结束了遥远的中国之行后,年7月底,霍金去了瑞士的日内瓦。在那里,他得了严重的肺炎,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那样在死亡的黑口袋里挣扎了几个星期。幸运的是,他从口袋的一端活着出来了。此后他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了,需要不间断的护理。他的气管被切开了,声带下方植入一个呼吸装置,并因此完全丧失了说话能力。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依靠电脑键盘和语言合成器与他人交流,且更愿意被人看成是一个正常人。年第二次来中国时,他还能用两三根能动的手指拨弄键盘。年第三次来中国时,他的手指完全被冻结了,只能依靠眼球和脸部肌肉的运动来“遥控”电脑。他的脑袋越来越歪斜了,给人以越来越无力的感觉,但他竟然发福了,至少下巴上多了一道赘肉,且似乎变得更幽默了。他无法拒绝他人的帮助,但拒绝他人的怜悯,尤其是廉价的怜悯。他还在做有关宇宙演化、时空未来之类的报告,或者对外星人、女人、地球末日之类的话题说些可爱的蠢话,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存在已不再具有物理学上的意义,而是具有另一种意义——成为人类与不幸命运抗争的象征。《大设计》的出版可以看成是这种抗争的一个具体例证。
4
《时间简史》初版于年,很快成为风靡全球的畅销书。迄今为止,它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总销售量超过万册,仅简体中文版就超过万册。这一当代奇迹既令人欣慰,也令人疑惑。因为任何购买此书的人若要读懂它,仅仅知道狭义相对论和薛定谔方程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广义相对论以及后来在量子理论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即便是最浅显的第一章,也不是那么易于理解(例如多数读者不会明白霍金对托勒密天文学所做的浓缩性描述:“托勒密模型为预言天体在天空中的位置提供了相当精密的系统。但为了正确地预言这些位置,托勒密必须假定月亮轨道有时候离地球比其他时候要近一倍,这意味着月亮有时看起来要比其他时候大一倍”。这话是什么意思,只有对托勒密理论的细节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明白)。尤其重要的是,书中涉及到的当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大多属于纯粹的理论和假设,并未经过实验和观测证实。这一奇怪的现象或许只能说明,人们并不是出于对知识的理解,而是出于对知识的信仰,尤其是这是一种艰深复杂、主旨宏大的知识,且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眩目的外衣。尽管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实证主义时代,这种对未经证实的理论的狂热和对权威的膜拜却构成了对实证主义的讽刺,使得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有关现代人是瞎了眼的巨人的比喻又多了一层含义。
现代物理学的一个巨大的诱惑是致力于找到一个终极的基本理论。这似乎是“为艺术而艺术”在另一个领域的翻版——为科学而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为理论而理论。这个终极理论之梦贯穿了二十世纪的大半部分,且仍将持续下去,最后是否会演变成一则标准的西西弗斯的故事,亦未可知。很多人试图将自然界中四种基本的力——电磁力、弱力、强力和引力——统一起来,且有望完成前三者的统一(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已完成弱力与电磁力的统一);另一些人则对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理论——描述小尺度世界的量子力学与描述大尺度世界的广义相对论——的不调和感到不安,试图用一种理论把它们融合起来。“霍金辐射”是初步尝试这种融合的结果,用量子理论处理宇宙的开端是更雄心勃勃的尝试。霍金的工作虽然富于启发性,却远未抵达终点,不过他本人却意外地完成了另一种融合——小尺度的个人传奇与大尺度的大众传媒的融合。当《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大设计》等在畅销书的排行榜上长期驻留时,当他在剑桥的办公室被重建于好莱坞的摄影棚中,当火爆的连续剧《生活大爆炸》中的“谢耳朵”在他面前直挺挺地晕倒时,此时的霍金不是影视明星,却胜似影视明星。很多明星不能做到在所有的国家都受到欢迎,但霍金的轮椅却可以从容穿过不同意识形态的藩篱,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赢得掌声。业内人士对他与牛顿、爱因斯坦一起打桥牌的玩笑所包含的暗示一笑置之,并不当真。在多数人眼中,霍金的成就不但不能与海森堡、狄拉克、费曼相比,亦不如引领第二次弦理论革命的威滕(EdwardWitten)。他们对宇宙的波函数信心不足,对弦理论的优美结构、丰富内涵以及威滕深邃的数学直觉更感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设计》中,为霍金情有独钟的宇宙终极理论的候选者M理论,其主要推动者正是威滕,但是两人的公众知名度却有着霄壤之别。
年,当康德完成对“道德的最高原理”的哲学阐述后,遽然发现此时的哲学已被连根拔起,“无论在天上或地上,都已经没有任何依靠和根基了”。近代科学的实验原则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其免于古老的形而上学所必然遭遇的根基不牢的处境。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当致力于大一统理论的物理学家愈加沉湎于眼花缭乱的数学技巧,且习惯于在高维时空(26维的弦理论,10维的超弦理论,11维的M理论)游荡时,这门学科似乎再次面临康德式的处境,亦即存在被连根拔起的可能。尽管很少有人会否认开尔文勋爵的看法——数学是惟一的好的形而上学,这种完全脱离实验的“清谈”式研究却不免引来激烈的批评。与温伯格齐名的格拉肖(SheldonGlashow)挖苦这种“万有理论”不过是中世纪神学的改头换面,其无聊程度令人想起中世纪的人们争论一根针尖上能容纳多少天使跳舞的问题。劳夫林(RobertLaughlin,凝聚态物理学家)则认为弦理论“是一个陈旧的信仰体系的悲剧性结果”。
年,有人询问现代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的奠基人费曼(RichardFeynman)对“超弦”(弦理论的一个改进版)的看法,垂垂老矣的费曼思维依然敏捷,他直率地说他不喜欢它,“我不喜欢他们不做任何计算,不喜欢他们不检验他们的思想,不喜欢任何与实验不符的东西”。费曼认为,这不是研究风格或方法不严谨的问题,而是这件事本身太困难,所以他们无法做出一个精确的预言——不是因为粗心,而是力所不及。这类批评自然也适用于霍金的宇宙的波函数,以及他所推崇的、目前也的确更值得期待的M理论。于是乎,年9月位于欧洲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启动便成了拯救物理学的一件大事。人们对这个耗资不菲的庞然大物翘首以待,希望它做出一些切实的发现。有关霍金与希格斯打嘴仗的花边新闻更是广为流传:希格斯希望LHC能够发现标准模型所预言的最后一种粒子——希格斯粒子,而霍金则以习惯性的美元打赌希格斯的希望落空,LHC注定不会找到希格斯玻色子(后来的进展表明,霍金输掉了这美元),不过假如它发现了微型黑洞(microblackholes)的话,将会使他非常高兴,尽管LHC的能量还是不够高。
5
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万神殿里供奉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卢瑟福,普朗克,狄拉克,薛定谔,费曼,费米,朗道……霍金不在最耀眼的之列,却很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位。半个世纪前,剧作家尤内斯库哀叹作家和诗人不再因其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被尊为先知和预言家,但先知和预言家并未消失,只不过不再是荷马、但丁、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托尔斯泰之类的人物。例如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公认的先知。当狄拉克试图成为类似的先知时,另一位物理学家泡利忍不住出语相讥:“狄拉克有一种新的宗教。这种宗教里没有上帝,而狄拉克是它的先知。”在朗道五十岁生日时,有人把他的十项发现刻在两片大理石石板上,称之为“朗道十诫”。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霍金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一位先知,一位半神(demigod),一位能够接近宇宙终极秘密的大祭司。在临近生命终点时,他对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强人工智能的警告显示出了惊人的洞见:“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事。我不得不说,是好是坏,我们仍不能确定。”在年底的视频中,霍金如是说,令人想起爱因斯坦对他们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核子武器的警告。此时的霍金也的确像一位先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科学技术即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到了20世纪末,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地球村复又成为一个everything-but-silent的小世界。身处两者的交集中,有太多的光环、太多的飞短流长围绕着他,便成为无可逃避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霍金和他那挂满古怪仪器的轮椅俨然成为一尊庄严肃穆、四处移动的雕像;不仅是一尊移动的雕像,也不仅是一尊会呼吸的雕像,他就是偶像,偶像缺席时代的偶像。这是一些过于热情的好心人的错,不是他的错。当旧的神祇消失后,人们往往会用新的神祇取代前者留下的空位子。虽然如此,在霍金的一生中,我们还是可以从纷繁的表象中分辨出某种简单而重要的东西,即集人类处境的两个极端——躯体的渺小脆弱与思想的广袤无垠——于一体的动人情形。
霍金:宇宙空间为什么是三维的?图片来源:pixabay
爱因斯坦强烈反对宇宙由偶然性制约的思想。他的感受可用他的一句名言来概括:“上帝不掷骰子。”但是所有证据都表明,上帝是位地地道道的赌徒。宇宙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随时都有骰子不停被投掷,赌轮盘不停旋转。赌场老板在每次骰子被掷或赌轮盘旋转时,都有赔钱的风险。但是赌了大量次数,各种输赢就被平均了,而赌场老板确保它们的平均对自己有利。那就是为什么赌场老板这么富有。
宇宙也是一样。当宇宙很大时,存在巨量掷骰子行为,结果平均到人们可以预测的程度。但是当宇宙非常小,在宇宙大爆炸附近,只有少量掷骰子行为,而不确定性原理就非常重要。因此,为了理解宇宙的起源,人们必须将不确定性原理并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至少在过去的30年里,这一直是理论物理学的巨大挑战。我们尚未解决它,但取得了很多进展。现在假设我们试图预测未来。因为我们只知道粒子的位置和速度的某种组合,所以我们无法对粒子的未来位置和速度做出精确的预测。我们只能为特定的位置和速度组合赋以概率。因此宇宙的特定未来有一定的可能性。但现在假设我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过去。
鉴于我们现在可以做出的观察的性质,我们所能做的全部就是将概率赋予宇宙的特定历史。因此,宇宙必然拥有许多可能的历史,每个历史都有自己的概率。存在一个宇宙的历史,英格兰再次赢得世界杯,尽管概率很低。宇宙有多个历史的观点听起来可能像科幻小说,但它现在已被接受为科学事实。这要归功于理查德·费曼,他曾在极具声望的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并在附近的脱衣舞酒吧打邦戈鼓。费曼理解事物如何运行的方式是,给每个可能的历史分配特定的概率,然后使用这个思想做出预测。它预测未来的效果非常好。因此我们认为它也可以倒推过去。
宇宙边界条件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与费曼的多重历史的思想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理论,它将描述宇宙中发生的一切。这个统一理论将使我们能够计算出宇宙会如何演化,只要我们知道它在某时刻的状态。但统一理论本身并没告诉我们宇宙是如何开始的,或者它的初始状态是什么。
为此,我们需要额外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被称为边界条件,它告诉我们在宇宙的边界,即空间和时间的边缘发生了什么。不过如果宇宙的边界只是处于空间和时间的正常点的话,我们可以越过它并宣称超越的领域还是宇宙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宇宙的边界是锯齿状的边缘,那里的空间或时间被压缩,而且密度为无限,那么要定义有意义的边界条件就非常困难。所以尚不清楚需要什么样的边界条件。
然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吉姆·哈特尔和我意识到第三种可能性:也许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边界。乍一看,这似乎与我前面提到的几何定理直接矛盾。这些定理表明宇宙必须有一个开始,一个时间边界。然而,为了使费曼技巧在数学上得到很好的定义,数学家们发展了一个叫作虚时间的概念。它与我们所经验的实时间无关。这是一个使计算成立的数学技巧,它取代了我们经验的实时间。我们的思想是说,在虚时间里没有边界。这就使试图发明边界条件没有必要。我们把这个思想称为无边界设想。
如果宇宙的边界条件是它在虚时间中没有边界,那么它不止存在一个历史。在虚时间里存在许多历史,其中每个都将确定在实时间中的历史。因此,我们拥有极丰富的宇宙历史。是什么从宇宙所有可能的历史中挑选出我们生活其中的特定历史或一组历史呢?
宇宙的人存原理
我们很快注意到的一点是,这些可能的宇宙历史中很多不能经历形成星系和恒星的次序,后者对我们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也许智慧生命会在没有星系和恒星的情况下进化,但那似乎不太可能。这样,我们作为能诘问“为什么宇宙是这样的?”的生命存在这一确凿事实本身就是对我们生活其中的历史的限制。这意味着它是少数拥有星系和恒星的历史之一。
这是所谓“人存原理”的一个例子。人存原理说,宇宙必须或多或少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因为如果它是不同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人在这里观察它。
许多科学家不喜欢人存原理,因为它似乎只比虚晃一招稍好,而不具有很强的预言能力。但是人存原理可以给出一个精确的表述,它在处理宇宙起源时似乎必不可少。M理论是我们完备的统一理论的最好候选者,它允许非常大量的可能的宇宙历史。大多数这些历史非常不适合智慧生命的发展。要么它们是空的,要么是过于短命的,要么是过于高度弯曲的,或在其他方面出错。然而,根据理查德·费曼的多重历史思想,这些无人居住的历史可能有相当高的概率。
斯蒂芬··霍金(StephenWilliamHawking)
作为人存原理威力的一个例子,让我们考虑空间方向的数量。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中是一个常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三个数字来表示空间中一个点的位置。例如,纬度、经度和海拔。但为什么空间是三维的?为什么它不是两维、四维,或其他一些维数,如科幻小说中那样?事实上,在M理论中,空间有十个维度(这理论也具有一维时间),但人们认为,十维空间方向中的七维被卷曲得非常小,留下三维大而近似平坦的方向。它就像一根吸管。吸管的表面是二维的。然而,一个方向被卷曲成一个小圆圈,因此隔开距离看,吸管就像一根一维的线。
为什么我们不生活在一个历史中,其中八个维度被蜷缩得很小,只留下我们注意到的两维?原因是,两维动物将难以消化食物。如果它像我们一样,有一个直通的肠道,它就会将那只动物分裂成两部分。这个可怜的生物就被分解了。因此,对于任何像智慧生物这样复杂的事物,两个平坦的方向是不够的。
三个空间维度有一些特殊之处。在三维空间中,行星可以在恒星周围具有稳定的轨道。这是服从由罗伯特·胡克在年发现,并由艾萨克·牛顿详细阐述的引力服从平方反比定律的结果。考虑两个物体在特定距离处的引力,如果该距离加倍,则它们之间的力减到四分之一;如果距离增加3倍,则将力除以9,依此类推。这导致了稳定的行星轨道。现在让我们考虑四个空间维度。万有引力就会遵循立方反比律。如果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加倍,那么引力将被除以8,3倍则除以27,如果是4倍,则除以64。这种立方反比律的改变使行星在它们的恒星周围不可能拥有稳定的轨道。它们要么落入它们的恒星,要么逃逸到外面的黑暗和寒冷中去。同样,原子中的电子轨道也不稳定,这样我们所知道的物质就不会存在。
因此,虽然多重历史的思想允许任何数目的几乎平坦的方向,但只有拥有三个平坦方向的历史将包含智慧生命。只有在这样的历史中这个问题才会被提出:“为什么空间具有三个维度?”
这段对宇宙形态的思考,节选自斯蒂芬·霍金生前的最后著作《十问:霍金沉思录》。
这是一本霍金留给世界的临别礼物。他经常被科学家,科技企业家,高级商业人士,政治领袖和公众问及他对当前一些“大问题”的看法。对于这些“大问题”的解答都被保留在一份巨大的个人档案里,这本书的内容都来自该档案。书中主要是简答关于人类和宇宙的10个大问题,其中6个问题深深植根于他的科学领域:
上帝存在吗?
一切如何开始?
宇宙中存在其他智慧生命吗?
我们能预测未来吗?
黑洞中是什么?
时间旅行可能吗?
另外4个则展现了他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我们能在地球上存活吗?
我们应去太空殖民吗?
人工智能会不会超过我们?
我们如何塑造未来?
霍金认为宇宙没有起点,但是有物理学家不同意年,史蒂芬·霍金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理论,以解释宇宙如何从无到有。但是两年前的一篇论文对此提出了质疑,宇宙学家们纷纷”站队“,这场争论今天仍在继续。
图片来源:MikeZengforQuantaMagazine
来源QuantaMagazine
撰文NatalieWolchover
翻译阿金
审校戚译引
转载请注明:http://www.hujingahj.com/aqxw/46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