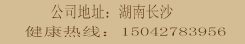一月的湘潭,细雨挟持了寒流与北风,盘踞一方,丝毫未有离去的打算。凌晨五点的被褥,意志薄弱若吾辈者,本无法抗拒。它十几年前就离开了,然又一次将我从梦中惊醒。它比初恋更让人难以释怀。
四平,某次回寝,室友在争论高考到底是6号还是7号开考,我说7号,但仍有人不信,我补了一句“我考了三次”,于是无人再质疑了。
年,每一个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人都与这个年份很搭。这次高考时间提前了一个月,之前是7月7日。湖南第一次采用3+x考试模式。这两样是之前就知道的。所不知者,一种叫“非典”的东西考前几个月就开始肆虐北上广等大城市,千里之外的农村中学也不能置身事外,教室每天都消毒,量过体温进考场。此外,据说有些人打开数学试卷就懵了,此科结束就有不少人弃考了。事实上,这一年数学题是有史以来最难的,能及格的人后来基本上都去念重本了,当然,我是例外。数十年未有之大变局,都被我赶上了,见证了历史,真是幸运。
年初中同班同学有几十人进了重点中学。一中在县城,理科力量强,开放管理,学风差;二中在五峰铺镇,大农村,文科好些,封闭管理,学风好。我考了分(总分),意气风发,就如那周郎破曹而归。怕自己学坏,选了二中。
这个分数可以进市二中,但要预交块保证金,说考上一本就退钱,有二位同学去了。当时的西瓜是三毛钱一斤,做小工是十五块一天,一学期的学杂费是两千元左右,每天菜饭费约三块五。我记得第一学期的学费还是从外公那里借了几百元才凑齐的。
父亲大人觉得读书主要靠自己,在哪里念都一样,他觉得其母校四中就不错,就在隔壁村,离家还近。父亲是文革后期念的高中,这种观点放在当时的确是颠簸不破的。当时,我们家族就属他文化层次最高,但他的的确确念了一回假高中,因为不需要参加高考,劳动、运动的时间远多于课程学习的时间。小时候喜欢翻箱倒柜,却没有找到他留下的任何书籍,《毛选》都没一本,甚是失望。
当然,那个时候,元在我们家族中也并非天文数字,二叔、四叔随随便便就能拿出。主要是我没那个意识,认为除了湖南师大附中,其他中学估计也差不多。父亲嘛,最怕欠人人情,尤其是自己兄弟的。
高考结束后就知道情况不妙,分数出来后才知道有多糟糕。仅得分,与二本线()尚有一段距离。这与老师同学们期望的北大,似乎有点远了。终于体会到楚霸王在乌江边徘徊时的惆怅。愁比烟雨浓,整个假期都没有心情好好放牛,但我还是比牛瘦得快。
能预知的伤都是皮外伤。都说模拟考试的题目比高考难一些,最后一次模考明明考了多分,不出10天就缩水分,19岁的脑子一下子的确难转过弯来。奇耻大辱。
其实被分数伤害已是司空见惯。刚进高中那学期数学测试,几乎都是不及格。当时幼稚的头脑一直在纳闷:初中数学很少低于90分,怎么一下就变差了。只能说念初中时,母校扎扎实实贯彻了义务教育的方针,严格按照中考考纲来教学。义务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真的难以答好为应试教育者准备的试卷。念书以来的成绩排名很少在前三以外,到了高中就邪门了,十几名到几十名,每况愈下。愈挫愈颓。多年以后才明白,不是自己太挫,而是对手太厉害,能坐在这理科重点班的,谁在初中不是佼佼者。
念书三十年,前几天刚拿到高等教育从业资格证书,算是正式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师身份的转变。一路走来,宠我提携我的师长不少,真正让我畏惧的老师只有两位,一位是小学六年级班主任林素梅老师,一位是高中班主任谢晶老师。就算现在碰到,也难保后背不出冷汗,这是一种刻进灵魂的畏惧。生性胆小,最惧“暴力”,尤其是言语上的,虽然绝大多数时候,自己并非打击对象。
谢老师是班主任兼物理老师,但在所有科目中,我的物理成绩最差,似乎很少及格。有一件刻骨铭心的小事,高一第一学期晚自习,后排曾德勇挠我的背,想借笔一用,转头递笔一幕被窗外巡视的班主任撞见,他当着班上同学们面冲我发飙“周海锋,你不学可以出去!”那响动不说能够揭翻对面四合院的瓦片,隔壁班关着门肯定能听到。你说我这样一位一直被宠大的三好学生,如何能承受这不白之冤,但也只能用体热脸红来应对这不白。毕竟,当时对方气场强大,我一丝辩解的勇气都没有。熬了两年,高三第一学期直接将课桌搬到楼下的文科班。走时没有跟谢老师打招呼。后来在校园也有邂逅,彼此一笑,并无言语,亦无恩仇可泯。
来到文科班有重回人生巅峰的感觉。虽然数学也常不及格,但很少有比我分数高的,真的假的围着问问题的姐姐妹妹的确不少,来者不拒。历史、地理和政治学起来也是得心应手,没几个月就和复读班的高手水平差不多了。外语似乎也还可以,常在分左右徘徊。班上有一个省三好学生名额,评上者高考可加5分,陈正秀老师根据平时成绩(主要据会考成绩)圈定我和赵文翔,然后让同学们投票,我胜出了。可惜我辜负了同学们的信任,这5分在我这里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若是他得了,中国说不定就会多一位优秀律师。他离西北政法的录取线也是5分。
有次历史测试,我拿到的试卷漏印了最后一道20分的大题,但还是得了88分,是三个文科班里最高的。莫宏春老师为此特意将我叫到教室外边聊天,说高考时一定要先把试卷看一遍,看是否完整,不能犯低级错误。
老师们宠着,同学们仰望着,在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氛围里愉快地度过了高三。
失眠是否影响发挥,我不太确定,向来倒床就睡着,但那两晚的确长。最后一门是英语,考完后就觉得重本没戏了。虽然除了数学,其他试卷都答完了,但有不少答案是在纠结中写上去的。
9号早上在校园内碰到吴小陆老师,告知考试情况,他安慰我别担心,万一不理想,再来一年。他请我在校外吃了一碗面,味美,一直不曾忘记。
三个班只有三人上了二本线,估计是校史上少有的。选择在本校复读者有八九十人,我是最先报到的,班主任吴小陆老师委以班长重任,还格外关照,让我住进他的煤球房。入住之日他说:“今年的县文科状元就住这里。”住着住着,黄涛从临沂学院、银科从县一中过来了,我一个人一间,他两一间,床面对面摆着。
这一年我把多半时间花在英语上,数学成就依旧差,但数学与努力程度关系不大。买了一本大学四级英语词典,睡前就记。有开门锁门任务,六点以前就到,十点左右才离开。自认为还是很用心用功的,平时的模拟考试成绩也不错。结果我们三人都没考好,看来是煤球房的风水变了。
这一年黎一杰老师上数学课,他同时还兼了理科班的课,有一次考完后我依旧去他他手里拿试卷,随口问了一句,“不知这次及格了吗?”“你要是及格了还了得!”黎老师建议我们班同学最后一道题可以不做,说那道题是给考清华北大的人准备了。课上他也从来不讲解那道题。当时看来,似乎稍稍伤害了某些同学的自尊,但的确是因材施教。
在二中考了两次,考完后总觉得数学考得不好,其它还行。可结果却恰恰相反。除了数学成绩差可告慰以外,其他科目都不能原谅。能够做对的题目,都没有错,已是难得。每次最后两道题,我都不知道题目是什么。
年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遭受的打击远远大于上一次。上一年普遍没有考好,包括理科班一些成绩很优秀的同学,或去了一所距理想甚远的高校,或选择再来一次。这一年,除了住在煤球房的三人,其他人貌似都超常发挥了。县文科状元也在班上,最后去了湖大法学院。班上分以上的有三人,上了一本线的有近10人。我这分数,还差二本线1分。银科也没过二本线,黄涛只过线7分。黄涛是从大学办了退学手续回来复读的,压力比我们更大。蒋友娟考完当晚就在操场上把书焚烧了,直接坐车去深圳打工,觉得自己考不上二本,结果上了一本线,去了湖师大中文系。吴舞艳感觉自己数学不会超过50分,居然及格了,最后去了福建师大中文系。
我一直觉得上湖师大之类,如探囊取物一般,从结果来看,就是自视甚高。接到了怀化学院的通知书,吴小陆老师建议我去念,不要再复读了,并说我可能真的不擅长考试。现在看来,吴老师识人甚明。就传授知识方面而言,四平师院和怀化学院的区别真的不大。当然,不同地方碰到的老师必不一样,他们会影响今后的道路。考上二本,班上80%同学的梦想。我们三个却不甘心止步于此,又一次选择复读。
黄涛去了县一中,我和银科去了邵东经纬试验学校。确定到经纬以前,我和银科去了科达、振华和创新,那时还没有正式开学,创新的门都没进,振华和科达均有老师接洽,很欢迎我们这种人来复读。科达的尹老师很热情,请我们吃了午饭,并让我暂时住在他办公室。银科当天就返回了,我住了一晚也拎着铺盖回家了。二校均在市区,校园也很小,不喜欢。暑期一直呆在家里,干点农活,放放牛,直到8月22号才去经纬报到。
经纬只收了元学杂费,享受半价待遇,上了一本的可全免。班上如我这种情况的有20人左右,大大的教室,挤了多人。私立学校高薪聘请过来的老师水平都极高,更难得是有情怀,把教学当成一种事业来经营。一群失落的人天天在一起,抱团取暖,日子也没有那样难过。上了大学的同学也没有忘记我们,不时写信打电话过来安慰加鼓励。校园很阔,里面有橘林。班主任朱老师是一位退休教师,不上课,专门处理各类杂事。管理特严,半个月休两天,平时出去需要班主任批路条。同学来自九县三区,也有其他市的,比如双峰的有好几个。
海平比我还晚来,是我介绍的。当时班主任说实在没有地方摆桌子了,我说对面的角落里还可以放一张。有一段时间,我和海平四目相对,脖子扭转三四十度才能看到黑板,但毫无怨言,谁叫我们是想听清老师说话的高人呢。直到凭借模考成绩选座位,才扶了正,但也不好意思选中间的位置。这一年海平进步最快,之前两次从来没有上过三本线,这次考上本科,是质变。我和银科也进步了,但还是遗憾了,都没有上重本线。再也不来了。黄涛考得不错,终于考进了湖南大学法学院,算是替我们去读了重本。
这一年的二本线是,一本线是,我差重本7分。想去的地方分数都不太够,胡乱填了几个。填吉林师大是吴舞艳建议的,她室友就是吉林的,说那个学校不错。我代表湖南来到了吉师中文系,此专业每两年在湖南招录一人。
那一年的成绩是经纬创校以来最差的,最高分仅能入对外经贸大学,或许是我和银科的到来,又一次改变了此间风水。考前班主任还带领大家拜了大成殿的孔子,估计祭拜时孔老夫子正在午睡,丝毫不知大家的诚意。
现在看来,在邵东复读最大的收获不是高考分数提高了几十分,而是认识了贱内,真是造化弄人。
高考年年有,余痛未曾去,一直想着,痛着。最后逐渐认清一些事实:首先,自己真的不适合考试。患得患失,大考前必失眠,一直到考博时还是如此;数学题都要算两次才放心;涂答题卡总担心没涂上。这些似乎也都可以归结为强迫症,是一种病。其次,明白自己智力一般,数学成绩就是证明;完全没有学习语言的天赋,在英语上花费了海量时间,效果却甚差,后来考研又一次被英语羁绊,碎了去西子湖畔一游的梦。如果使劲找,自己身上也还算有优点的,能坚持、好奇心强。比如追剧,同寝的人就无法超越,迷上了,凌晨三四点都不睡,也有通宵看完结局再睡的时候,现在依然如此,比较难得。
历年高考成绩一览表
年份
语文
数学
英语
文综
总分
95
90
82
98
84
97
文科可选择的专业本就不多,现在看来正好可以补补课。左思右想,还是对历史有感觉,虽然最后转入历史也是偶然,算是歪打正着吧。学习历史需要对过往种种抱有兴趣,自小就喜欢看古装剧,不太喜欢看现代剧。
高考的后遗症去年又发作了一回。往一所双一流高校投了求职材料,院里通过了,校学术委员会嫌弃我的第一学历,不敢录用。他们是对的。
爱过,恨过,有期待,有失望,我依旧坚信高考是最好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智力水平、心理素质、勤奋程度都会在分数上体现出来,很公平。这几年有机会与本科就读清华北大的朋友一起共事,发现他们确有过人之处,能考上绝非运气,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差异,可能是后天努力无法抹平的。好在自己现在从事的行当,很多工作不需要绝顶聪明就能胜任。
三次高考,是执着,是豪赌,是迷惘,是不甘,还是愚蠢,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最可悲,东流水可西回,少年时不再来。稍可告慰的是,通过不断反思高考,逐渐认识了自己。
如今种种,均拜高考所赐;过去种种,并未烟消云散。十几年来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吃过的苦,受过的辱,都与它有或多或少的关系。高考就是一个魔鬼,只需触摸一次便萦绕你一生,一而再再而三招惹它的人,它定要陪你三生三世,或有桃花。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一日于湘潭夏荷苑
一蛮
转载请注明:http://www.hujingahj.com/aqxw/9874.html